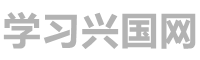“印度之行:印度是民主的典范?”
前幾天我被要求編輯教材,所以讓學生找了復印件,但是收到的資料各種各樣,讓我選了各種各樣,很煩。 不應該做英語精讀資料,但有引人注目的講稿。 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印度經濟學家阿馬蒂亞·森( amartya sen ),同時也是劍橋、哈佛等多所大學的名譽教授,在新德里的民主大會上發表了主題發言。

20世紀人類最重要的轉折點是民主主義的崛起,從這個意義上說,世界各地嘗試了各種形式的民主主義,但大浪淘沙,希臘式民主主義留下了微薄的成果,升華為人類統治的普遍模式。 雖然可以懷疑19世紀民主主義是否適合某個國家,但在20世紀之前這樣提問是錯誤的。 世界上數十億人的歷史、文化、經濟狀況千差萬別,民主不是與國家相適應,而是與民主相適應,但民主主義遲早會像惠及所有人的計算機默認計劃一樣,在20世紀,民主主義默認了。 哇,民主主義也很獨斷哦。

他以印度為例說明了民主主義的優越。 獨立前,英國人擔心印度人管不好自己。 獨立后,印政府用憲政處理政治分歧,通過選舉消除民族矛盾,在短短半個世紀內取得驕人成績,令亞洲鄰國敬仰,言辭鑿鑿,不容置疑。
他有各種各樣的記載,但民主主義都是芝麻開門的咒語,不會不利。 但是,在兩年前的印度旅行中,我一直在懷疑印度民主主義是什么。 那和觸目驚心的現實生活是什么關系? 雖然逗留時間很短,光彩奪目,但我沒有體驗過希臘的民主主義。 現在民主人神共佑,所有人口都一定在呼喚,但心里想的恐怕是南轅北轍,名副其實。

從北京經由香港十幾個小時后飛往孟買是在凌晨兩點。 孟買的時區也比北京晚兩點五個小時。 這個時間本來應該很冷,但是機場人潮涌動,肩膀手指相連,如同夸張一樣沸騰。 印度人午夜去機場的派對嗎? 機場里車輛往來頻繁,就像交通高峰期一樣。 車馬龍是個比喻,但在這里很寫實。 奔馳轎車和牛、馬車并排行駛,自行車在拖拉機和摩托車之間穿梭。

第二天早上,一看到街景,兩側躺著很多人,在毒天的頭下,老人走進污水溝洗著鐵餐具,動作很慢。 鵝黃色寬松的袖子又臟又寬,頭上的布看不出本色。 后面有個孩子在跳。 一個年輕的女人半睡在人行道上,一家人剛吃了早飯。 街上到處都是在下水道做飯洗碗的人,蒼蠅蚊子嗡嗡地亂飛。 沿著破敗的街道前進,眼里沒有污垢,城市就像難民營一樣。

邀請方說,我們住的地區是濱海區,非常好。 市里也有貧民窟,但是不給我們看。 我還以為電影《貧民窟百萬富翁》( slumdog millionaire )的外景地是制作的,但現在知道是實景。 拍攝地點是孟買的達拉維( dharavi )貧民窟,那里人口超過百萬,有四個規模更大的貧民窟,據說城市生活人口的55%住在垃圾堆里。

這部電影上映后,貧民窟變成了孟買的風景,每年游客以30%的速度增加。 印度人討厭獵奇( voyeuristic )心理,不許游客拍照。 但是,內心陰暗的游人依然在垃圾堆、污水攤子、腐朽的鐵絲和破碎的鋼管之間頑強地漂浮著。 在用腐朽的木板、舊木箱建成的簡易房間的縫隙里,有一位尋寶般的游客,饒有興趣地環顧著周圍。 不經意間,遇見了眼睛在房間里半裸著躺著的當地人,在對視的瞬間,自己先是不自然地手足無措。

海邊很多人在玩水,海水很暗,礁石也很黑,人在傲慢的太陽下很黑。 阿拉伯海海面一片空虛(/k0 ) ),陽光下也仿佛一片黑色的氣氛,仿佛毒天刺眼的白光也有自己的影子,這不是典型的海濱麗景。 回國后,從行李箱里拿起衣服,看到下擺領口上有黑邊,發現在印度的中午,空煤氣充滿了焦炭粉塵。

到了晚上,天空沒有星星也沒有月亮。 街上混凝土上人山人海,有人睡得亂七八糟,有人雙手枕著枕頭,有人家庭縮成一團,孟買的夜晚一片寂靜。 標記和混合; 吐溫在孟買旅行時,看到了和眼前一成不變的情景。 我們好像走在死亡的街道上。 空寂靜的街道沒有任何生命跡象,烏鴉也不吭聲。 數百名印度人四腳朝天地躺在地上,似乎在裝死。

但是,孟買的形象并不單一。 的面排列在一起,在多個空之間重疊。 只是排隊的方法很不可思議。 印度教寺院與天主教鄰接,摩天大樓下面是條貧困的街道,奢華的洋房別墅外面是一條骯臟的貧民窟。 同一個空之間,不同階層、文化、種姓、觀念、優點、宗教、身份重疊,雖然平行共存,但蜷在奢華腳下生活的赤貧讓人放心,彼此平靜 相反,這里是全球資本、世俗勢力、狂信、地方民族主義、等級制和階級對抗的角斗場。

獨立之初,各種勢力相互擠壓、沖突,多次發生暴動、屠殺、仇殺。 印度流亡作家拉什迪用紀念印度獨立五十周年的復印件進行了概括。 一九四七年八月,獨立作為印度歷史的新起點,承諾了自由的黃金時代的到來。 半個世紀過去了,一九九七年八月的印度充滿了末日感,幻滅為獨立的新時代劃上了句號。 他回答的是尼赫魯獨立之夜的全國演說。 在這個午夜鐘聲響起的時候,世界還在沉睡,但印度將迎來生命和自由的覺醒。 50年前約定的新時代,會給包括工人、農民、賤民在內的所有人帶來繁榮、民主、進步的國家,不論任何信仰、種姓、階級,都分享平等的權利。

50年過去了,雖然殖民地遺產沒有清算,但繼承了英國人常用的分割統治之策。 獨立的印度無法處理印度教、錫克教、伊斯蘭教和基督教之間的沖突,也無法緩解高種姓、低種姓、無種姓、語言、方言之間的敵意,分裂是不可避免的。 看到獨立跡象的時候,印度教和穆斯林互不相讓,印度一分為二,巴基斯坦獨立的過程很艱難,50多萬人被屠殺,200萬人流離失所。 印度教徒還抱怨甘地溺愛和射殺了穆斯林,印度沖突持續不斷。 一九七一年,印度支持東巴的孟加拉族獨立,巴基斯坦重蹈印度的覆轍,分裂孟加拉國。 印度內部還多次發生語言暴動,造成無數死傷。 英迪拉總理·; 甘地20世紀70年代實施了全國緊急事態,1970年被錫克族暗殺。 兒子拉吉夫剛繼承首相,就被泰米爾猛虎射殺。

拉什迪的長篇小說《午夜之子》( midnights children,1981年) )虛構了以魔法的筆觸在獨立日午夜出生的孩子們。 電臺播放尼赫魯動人的演講,新生兒被扔進喧鬧的世界,他們感知、處世、成長的故事構成了印度建國的寓言。 這里沒有二維善惡黑白,也有非線性情節遞進,雖然不是家喻戶曉的時代史詩,但感受到了魔幻、神秘的歷史氣息。 籠罩在意識的洪流中,總是被歷史的洪流所裹挾,無助和幻滅到處漂浮。 在混亂的多樣性、零散的沙子一樣的印度社會,無法確定誰是強權的。 壓迫、暴力無處不在,社會關系松散,等級依然嚴峻。 就像你稱之為專制或民主一樣,結果是義不容辭的。

在孟買,吃喝有問題。 接待方說不吃開胃菜,不去普通餐館,一定要喝瓶裝水。 有一天中午,在酒店的餐廳要了冷盤,認為帶星星的酒店的衛生應該得到保障,結果馬上就見效了,一下子餓了。 擁有黃連素真是太好了。 沒有影響日程安排。 美國作家保羅·; 索( paul theroux )的《汽車大巴站》) the great railway bazaar ),微微一笑。 他去過一次美國駐德里大使館,撞到大使館人員去哈里斯看醫生,原因是便秘。 明明抱著四腹絕命,他卻莫名其妙。 有什么好笑的? 同行的官員約翰說,剛到印度的大腸桿菌讓他從肚子里跑了六天,為了省事就在廁所里睡了。 外國人在印度便秘,要怎么鍛煉腸胃呢!

茶后,擔任接待的女作家薩曼莎·; 蒙蒂( sharmistha mohanty )在閑聊,孟買的英文名字叫bombay,你是怎么改成mumbai的? 其實心里有答案,只是有點印證。 她嘆了口氣,說名字是一九九五年改的,是地方民族主義排外的結果。 她一副生氣的樣子,一句話也說不出來的表情,不方便深究。 北京的英文名原來叫peking,后來改為本土漢語拼音beijing,被殖民。

后來我才知道,印度的事情沒這么簡單,光是研究孟買改名的學術專著就有好幾本。 在外人眼里,地名的英文拼寫看起來不痛不癢,但對孟買人民來說,這是生活的轉變,從國際都市文化轉向了激進的排他性政治。 濕婆神軍黨( shiv sena )掌權后,動員底層印度教民眾,仇視穆斯林、婆羅門、全城市精英,階級、等級、語言、信仰沖突一下子加劇,政治生態超乎想象。 莫漢提議婆羅門,文化精英,家境富裕,她的苦惱一言難盡。

語言不僅是印度,也是信息表達媒介。 在有400多種語言、一千六百五十二種人種方言的國家,一代一代多次受到外國人的統治,堅守下來的只有語言。 印度人把信仰、古來流傳的東西、身份意識、文化感情都包含在語言里。 因此,從國大黨反英殖民斗爭一開始,就洞察了各地方、各民族的需求,承諾獨立后廢除英人劃定的行政區,按語言新建國家,得人心。

英國向上層強加英語教育,試圖將殖民地合二為一,但最終只有不到3%的精英熟練掌握英語,很多人與此無緣。 獨立后的印政府于一九五○年立憲,以印地語( hindi )和英語為官方語言,其他二十二種地方語言也正式采用。 英語只是一時的聯系語言,十五年遷移到印地語成為官方語言,行政區劃也以語言為主,呈現出舊態依然的新面貌。

但是,憲法一發表,除印地語以外的各國一齊反對,小語種紛紛謀求公共地位。 印地語從來不是語言之間的中介。 不如說,英語不受宗教的束縛,也不屬于民族。 一旦殖民統治明天變成黃花,英語就更容易被各方接受。 地方上發生了排斥印地語沙利文主義的運動,抗議聯邦政府的語言暴政。 印地語的缺陷也很明顯,寫作是梵文文化的文字,與口語相差甚遠,在文盲占大多數的國家難以消化。 另外,用語言進行國家建設也不現實,就像印度和印度之間被信仰劃分了國境一樣,人口的混雜引發了大規模的移動、武器斗爭、屠殺。

憲法一出,語言暴動( language riots )不斷,絕食抗議、放火、殺人、搶劫。 特別是一九六五年英語過渡期結束,印地語獨立之際,泰米爾納德邦爆發了大規模的反印地語暴動,造成七十多人死亡。 政府意識到語言是潘多拉的盒子,是反殖民化的利器,也是反中央政府的離心力,釋放出了足以瓦解新誕生國家的能量。 印政府匆忙停止憲法的實施,兩年后修改憲法,印地語和英語結果無限期擔任兩國官方語言。

孟買改名與語言建設國家密切相關,是地方和聯邦沖突的縮影。 一九五六年,尼赫魯宣布,由于擔心商業大城市孟買被馬拉蒂內陸農業拖累,它是馬哈拉施特拉格拉特邦的首府。 但是,說馬拉地語( marathi )的印度教徒不回應,騷擾和襲擊古吉拉特人。 警察出面鎮壓,殺死了80多名示威者。 被稱為孟買之戰。

犧牲的悲情激勵了地方民族主義,最終迫使聯邦妥協,馬哈拉施特拉獨立為單一語言的國家,以孟買為首府。 說拉丁語的內地農民涌入孟買,但無法與穆斯林和在南方接受教育的外省人競爭。 技術力量高、收入豐厚的各個職位被說英語的知識分子壟斷,馬拉地人只能苦干,抱怨外邦人搶工作。 列舉了如受歡迎的平面周刊、我們的“故事會”那樣,孟買大企業的干部都是穆斯林或南方人,當地人無法掌握的事情,一下子煽動了排外情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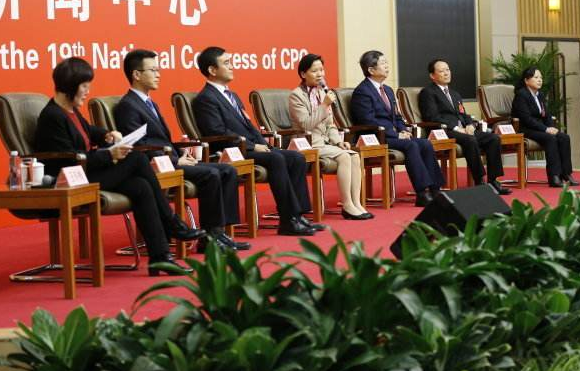
該雜志主編玫瑰·; 薩克拉門托bal thackeray看到人氣十足,棄文從政,于一九六六年搖旗成立濕婆神軍黨,三百年前舉起馬蒂國王希瓦吉shivaji的牌位,毀滅強大的莫臥兒帝國的武圣。 雖然綿羊建立了印度教的馬蒂帝國,但在佩什瓦時代,婆羅門的手落在權力旁邊,最終被英國人消滅了。 古代的戰神是飽含豐富象征意義戰勝伊斯蘭教徒的英雄,是被婆羅門的知識精英背叛,被英國殖民的殉教者。 印度教回歸波斯化前純潔的印度黃金時代的夢想,寄托在他身上。 所謂shiv sena,也就是綿羊的軍隊。 孟買大大小小的公園、街道中心廣場、車站、郵局,到處都沒有小雞持刀騎馬的像。

濕婆神軍煽動下層民眾排斥古吉拉特人、南方人、穆斯林、知識分子、中央政府等非馬拉地因素,孟買的階級、信仰、部落矛盾全面激化。 一九九二年至一九九三年間,印度教徒摧毀清真寺,燒毀穆斯林商店,奸殺穆斯林婦女。 印度的騷亂總是伴隨著強奸,印度女性實際上配合男性奸敵的私房展。 伊斯蘭教徒上街抗議,但孟買警察偏袒印度教,射殺200多人,城市陷入大混亂。 15萬穆斯林逃離孟買,10萬無家可歸,800多人被殺。 其次,穆斯林以極端恐怖主義報復,于一九九三年三月在市區十三個地方放置炸彈,一天炸死二百五十七人。 大爆炸震驚了全世界,孟買一夜之間成了絕望之都。 搜索大爆炸信息時,我們看到外媒報道血腥細節,印度媒體指責巴基斯坦為幕后黑手,但沒有提及前因后果。

這次濕婆神軍殘酷戰斗的形象深深地印在了人們的心中。 大家其實都明白這個強盜黑幫的本質,用的是印度教記者的說法。 他們確實是笨蛋,但我們的好笨蛋。 國大黨、右翼人民黨看起來比較負責、溫和、民主,但遠遠不及濕婆神軍強悍的監護人形象。

兩年后,濕婆神軍黨與人民黨結盟,贏得地方選舉,掌管馬哈拉施特拉州。 文化繼承英國化的孟買,城市的英文名被改成了印地語發音的mumbai。 國際機場、中央鐵路站(維多利亞站)都改成了絲柏,殖民城市變成了我們的城市,穆斯林、祆教、古吉拉特人都被踐踏,民粹主義政治大行其道。 阿馬蒂亞&米德; 在森比附歐洲的構想中,孟買的地方選舉讓人聯想到20世紀30年代的德國。

拉什迪將《午夜之子》改編成電影,并親自配上了外部聲音。 我被歷史神秘地銬著,命運無法擺脫,與同胞糾纏在一起。 這位出生于孟買富裕穆斯林家庭的作家,是一位虛構名叫希瓦( shiva )的兩位主人公的作家,名字一看就知道指的是濕婆神軍shiv sena。 另一位薩利姆( saleem )是典型的穆斯林名字,類似于作家的身世,有自傳的意義。

薩利姆似乎被希瓦欺凌,穆斯林被印度教排斥迫害。 希瓦成長為狂熱的反穆斯林軍官,女仆因此解開了他們身上的謎團。 她在分娩室做護士的時候,理想是取消社會等級,在獨立之夜用貍換太子,用殷實的穆斯林換印度教街頭藝術家的兒子。 巴希爾是穆斯林,薩利姆才是印度教徒,血統不純。 因為母親被英國人強奸了。

寓意直率:種族紛爭的根源是虛的。 希瓦知道自己是穆斯林時,反而迫害了同族。 小說暗諷濕婆神軍只會挑唆民族紛爭牟利,不在意非我族類。 編織波斯化和殖民化之前的回歸純粹印度的神話,也不過是避免印度百種混雜赤裸裸的現實。

從克什米爾到孟買,從阿格拉到卡拉奇,拉什迪在解決信仰沖突、階級對抗、信任與背叛、暴力與寬容等主題時,并沒有揭示宏大的歷史,而是讓獨立日出生的孩子們擁有魔法、占據未來、或 他們只是冷眼旁觀,沒有為國家效力。 這是拉什迪介入的方法,印、巴分治后,穆斯林政治身份分裂,是印度人還是巴基斯坦人? 身份的糾葛還使海外印度知識分子鳥瞰、繞行、比喻地講述歷史、憐惜自身的遭遇。

客居美國的霍米·; 也許不是,但他來自粢教家庭孟買,粢教長得像穆斯林,是專業化、收入穩定的少數派。 信仰、文化與許多人隔開,他們遠離社會政治,漂浮在上面,塑造出優雅的精英。 霍米&米德; 巴巴( hybrid identity )這個概念交錯在一起。 這是海外印度人后現代離散文化的寫照。 有條件移居海外,請世界傾聽印度的代言人,但不介入日常現實,與海隔離。 他們的敘述要么是魔法,要么是神秘,要么是抽象,要么是疏離。 理論中裂縫太多,充滿了破折號隱喻的間斷性空之間。 他們傾心的是全面世俗化、處于殖民時代無政府狀態的印度。

清晨打開客房的門,腳下有一摞英文報紙,文案大多是政黨紛爭和選舉攻防。 印度的英文報紙鄙視地方選舉的蠻橫、無理、惡性競爭,輕視底層和農民出身的政治家,滲透到公共行業,有著玷污了以前流傳下來的政治倫理和公共服務意識的莫名優越感。 有文案認為,婆羅門要全力以赴,牢牢記住自己的社會作用,不輕易干預政治,教化民眾,培育工業,這是功德圓滿的。 婆羅門以前傳說印度是最高種姓,現在種姓歧視是違法的,大城市忌諱它,極力淡化個人種姓背景,但它仍然是日常交往的潛規則。 雖然大城市婆羅門不再是祭司和精神領袖,但在充滿書香之前就流傳了下來,在知識界占很大比例,海外移民也很多。

印度知識分子面對令人沮喪的現實,離開象牙塔,穿梭于世界各大城市之間,喜歡進入國際學術,追隨海外后殖民理論,謀求印度陌生的生化和神秘化。 就像寶萊塢的歌舞劇一樣,輕快舞蹈的童話無法再現可以認識的真實生活。 馬蒂亞&米德; 森反復強調民主主義不是大多數人的決策,還有很多其他需求,這可能是印度的經驗之談。 知識分子有開放的國際視野,很多人不想看到決策的民粹主義政治。 這條路不通現代民主主義。 但是,自己不融入鄉土政治、言行不一的不自然的環境,才是第三世界民主主義的真相。 如果沒有大眾的參加,怎么能說是希臘式民主主義呢?

一九一五年甘地從南非回來,痛感印度階層的分化。 他也是海外知識精英,出身婆羅洲,在英國取得律師資格,在南非領域20多年,46歲回到祖國。 他問同胞:“上層精英壓迫廣大民眾和英國殖民有什么不同? 回來的第一件事,就是投身農村,了解事態了解民情,動員農民,督促城市工人進行不合作的反抗。 獨立后,他的追隨者尼赫魯迅速發展甘地的思想,在極端貧困、極端不平等的國家,公共政策強調共同快速發展,必須扶植貧困人口,幫助邊緣弱勢群體。

他的民主理念是形成堅定不移的世俗化、內部社會主義經濟、對外不結盟外交、國大黨的核心價值。 然后啟蒙文化上占大多數的文盲人口。 尼赫魯有自己獨特的社會主義觀念。 社會主義意味著所有階級和集體一律婆羅門化,最終消除階級差異。 這與舊婆羅洲的濟民理想沒有什么不同。

婆羅洲化會是怎樣一個漫長的過程呢? 多次下來需要多少耐力? 必須有像甘地和尼赫魯那樣有人格魅力的領導人。 他們一生打破信仰、種族、語言的壁壘,實施泛印度世俗主義,將大小王國、土邦、殖民地統一為現代共和國。 但是,在那之后,印度政治逐漸右轉,民粹主義綁架了賤民,右翼席卷了大眾。 濕婆神軍等地方政治家,吃盡了街上游蕩的幽靈般的賤民困頓,為他們訂制了馬拉地身份,崇尚信仰篤勵、血統純正、守土保護家尚武文化,從根本上挑戰了尼赫魯主義。

20世紀80年代,受過西方訓練的印度學者們,下沉后試圖進行基礎研究( subaltern studies ),產生了一時深遠的影響。 只關注被壓迫的少數、后殖民文化或者與同性戀研究有關等一般意義。 并不一定了解印度學者的獨特經歷:印度底層失語、知識分子從此被隔絕,絕非弱勢群體可以一言以蔽之。

雖說是研究的底層,但未必能轉移到研究對象,女作家娜揚·塔拉·; 薩加爾( nayantara sahgal )不僅生活在同一個次大陸上,在物質或心靈上也沒有共同點,精英表現出的焦慮也不是印度本身,而是自己的生存狀況。 如果當地人告訴你,城市不代表印度,你在哪里能找到真正的印度? 是農村嗎? 保羅和米德; 索爾確實去過村子,但同樣被拒絕,最多在骯臟的餐廳吃飯。 村民搬到了車站。 夜晚的黑暗降臨,車站變成了車站村( station village ),村民千萬別睡在站臺上倒下,外人去那里可能會和印度有很親密的接觸。 印度是多個indias,是交錯并存的多面體。 而且,印度是地理概念和文化符號,不容易適用現有的民族國家概念。

去德里的話,好像能看到印度的真相。 薩達姆神殿( swaminarayan akshardham )是2○○5年后建造的印度教新寺院,占地1萬公頃以上的大庭園。 用秋葵的沙子和漢白玉做的瓊樓玉宇,有000多尊精巧雕刻的神明,被柱廊包圍。 遠處綠茵連綿,附近看著蓮池的瀲滟,游客們搖著船,錯過了時間,為草木投下陰影而高興。 淡煙夕靄中,音樂噴泉的聲光紊亂,霓虹流動的期間,人影混亂。 除了鬼斧神工,還有高科技玄幻、3d電影院、激光投影、超大型屏幕。 這里曾聚集了3千多名藝術家、數萬名工匠歷時數年建成,被吉尼斯認定為世界印度教寺院中最好的。 圓明園極盡奢華之時才覺得美麗,但眼前美麗的景色,讓自己為淺學感到羞恥。 在奢華廟墻外,乞丐組成徒步黨阻止游客,伸出骯臟黝黑的瘦胳膊,但眼神呆滯。 說不定魂魄已經漂浮在大墻上,現世早就模糊了。 在這里,信仰生活才是真實可靠的,但知識精英被稱為普遍自由,涅夫的泛印度世俗化,僧侶和民粹主義深諳民情,不可匹敵。 他們把控制民眾信仰這種芝麻開門的秘訣,集中人民的財產,盡著人民的力量。

一八九六年標志·; 吐溫在印度旅行,記錄了蘇泰墓地,也就是新寡婦殉難的地方。 石碑上刻著夫婦一起死去的畫面,讓當地的女性很羨慕。 如果政府允許與吐溫同行,寡婦們將競相效仿。 這是光宗耀祖的好事。 作者感慨,多么奇怪的民族,所有的生命都是神圣的,憐憫蠑螈懶惰掃地,珍惜飛蛾紗窗的燈光,是一個只關心人命,不關心人命的令人費解的國家。 這是現代世俗文化的典型態度,在于了解印度的無能。

遠處安靜悠閑的牧羊人,倚著破廟破舊的壁畫打瞌睡。 一寸斜陽悠悠地持續在夜晚,夜晚日復一日。 印度在和他做什么? 國家對他有什么好處? 舊的自然生存狀態,讓市民這個詞太奢侈了,空太泛濫了。 法律教科書上的自然人,應該讓牧羊人解釋,他無法想象民族共同體,整體觀離他太遠了。 要從中央統一全國的工業現代化,在印度比駱駝更難穿針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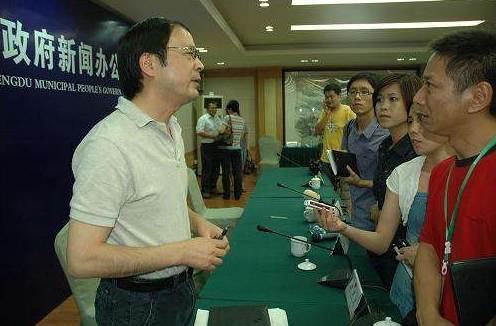
森的民主觀經不住推敲,與他不言自明的前提有關,但其實歐化的民族國家觀念并不普遍,中國人在兩千年前曾想象天下大一統,但未必會產生西式的國家觀。 在虛無的前提下,他把民主、憲政設定為默認的進程。 社會是機器,制度是應用,人類是物理世界的一部分,裝載不同的過程會產生不同的結果。 通過嫁接理想的制度,可以期待理想的社會,但在過去荒涼原始的固定力上沒有留下本來的位置。

相關名詞:
本文:《“印度之行:印度是民主的典范?”》
心靈雞湯:
免責聲明:學習興國網免費收錄各個行業的優秀中文網站,提供網站分類目錄檢索與關鍵字搜索等服務,本篇文章是在網絡上轉載的,星空網站目錄平臺不為其真實性負責,只為傳播網絡信息為目的,非商業用途,如有異議請及時聯系btr2031@163.com,本站將予以刪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