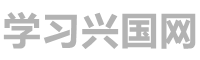“解璽璋”
原編輯:這是六年前發表在北京日報上的針對出版業改革的學術論文。 出版業完全市場化后,可能會發生各種矛盾,主要提出了如何保護我國的文化價值,誰為文化價值埋單等問題。
出版業是社會主義思想文化戰線上的重要行業,在這個行業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的積極作用、高舉馬列主義旗幟、更好地為廣大人民群眾提供健康向上的精神食糧等方面,確實是不可忽視的大問題。
但是,修正主義出現后,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筑,全面改變了旗幟,復活了資本主義。 巢下面有個完蛋。 出版業自然不是世外桃源,逃不掉。 指出出版業市場化以后的幾個具體矛盾,一是文化價值和市場價值的矛盾,比如如何防止低俗、低俗的垃圾出版物占領出版市場,能有力地保護哪些社會價值和文化價值高的出版物。 其二是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的矛盾。 在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市場效應時,出版業的社會效應如何避免受到影響和損害? 其三是公平與利益的矛盾。 這里涉及腐敗之風和廉潔自律的問題。 例如,防止單純的書號銷售和向各級領導干部的情書泛濫等。 其實,這個矛盾,那個矛盾,基本矛盾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個階級,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馬列毛主義和修正主義兩條路線的矛盾。 在現實生活中,出版業和其他各行各業一樣,已經染上了銅的臭氣,追求剩余價值,追求好處最大化,是整個領域的通病。 根源是經濟私有化、政治自由化,也就是資本主義化。 改革開放以來,許多重復馬列主義的學者,要出版自己的書,就必須自己掏腰包買書。 否則出版社會拒絕你。 這個還可以。 如果學者的書多少帶有修改和資金援助的色彩,那是國內出版社絕對不能出版的。 有學者哀嘆說,現在國內的出版業不如魯迅時代,魯迅等左派學者的作品還能在國內出版,沒有必要自掏腰包。 這種現象不值得我們深思嗎? !

2009年5月11日《北京日報》
出版圖書不僅滿足人們的閱讀費用,也承擔著文化傳承和文化積累的責任。 這種責任在市場行為中不太容易實現,有時相互矛盾。 出版業的完全市場化,作為市場主體的出版經營者在遇到這種矛盾時,會陷入某種不自然的狀況。 在這方面,國家和政府有不可避免的責任。 我們不能希望市場平等地接受流行的暢銷書和學術價值、文化價值高的書。 后者只是國家、政府或社會提供必要的保護。 在基金會體系不健全、發展迅速的中國,這種保護只能由國家和政府來進行。

但是出版業目前正在進行的這種改革似乎沒有考慮到這些事情。 出版業市場化如果忽視文化的保護,很可能會給國家和民族帶來不可挽回的損失。
最近一個時期,出版業的改革非常熱鬧。 根據信息出版總署的要求,到年底,全國所有出版機構,除人民出版社、民族出版社、盲文出版社、藏學出版社外,將完成全部轉制。 這意味著中國出版業終于告別了計劃經濟體制下的事業單位管理模式,成為具有市場主體地位的獨立經營單位。 這雖然不能從根本上處理中國出版業的問題,但仍帶來許多遐想,從中似乎看到了一線生機。

不完全市場:書號資源依然壟斷
一是認為可以實現我們多年來期待的出版業市場化。 有意見認為,出版物垃圾盛行不是市場化導致的,而是沒有市場化導致的。 很明顯,他們認為市場化會出很多好書。 這可能是誤會。 事實上,出版社的轉變只是從事業單位變成了擁有經營權的公司。 可以說具備了進入市場的前提條件。 說進入市場,也許太早了。 而且,真正的出版市場在哪里? 現在還是個問題。 即使只發行,或者選題、文案進入市場,唯一的出版資源仍然是計劃經濟,仍然是國家壟斷,國有和非國有出版機構不能公平享受的情況下,這個市場還不完整,缺失。

很明顯,我們不能對出版社的轉制抱有過高的期望。 畢竟,它處理的也是出版社內部機制的問題。 也就是說,出版社轉制有可能使其內部資源配置逐漸合理,調動其內部員工的積極性,提高工作效率,解放其內部生產力。 但是,如果不從根本上切斷對本期的依賴,他們依然寄生在本期資源壟斷這一人制上,出版社的面貌難以根本改變,本期的買賣也難以根除。 事實表明,國有出版社有相當一部分內部工作不足,人才、選題、資金等主要資源相當匱乏,再加上長期以來的內耗,普遍腎虛。 他們能夠參加市場競爭的程度很低。 但是,他們也必須迅速發展才能生存。 我該怎么辦? 一是要繼續銷售書號,借力民營出版企業,謀求快速發展;二是要開發短、平、快選題,為市場謀利益,為真金白銀。 想想那會是什么樣的情景。

完全市場化很可能導致出版垃圾化
什么樣的巨無霸式出版集團會變成什么樣呢? 他們通過上市也許能賺一點錢,但這樣的郎和合作的簡單組合,能否實現做大做強的初衷,還不容易說。 曾經也有好的出版社,出了很多好書,但勉強進入這樣的大規模集團后,反而失去了以前的活力,原來的出版資源也被集團整合,被集團消化了,所以不能再多了。 很明顯,這里看到的不是市場自發的過程,而是行政命令的結果,違背市場規律。 再者,如果出版公司明確為具有市場主體地位的經營單位,追求經濟效益、追求市場份額、追求利潤最大化也有其正當性,沒有理由反對別人賺越來越多的錢。 一點出版機構在所謂市場化之后就是這樣做的。 他們毅然放棄自己多年的出版理念、出版理想,以滿足市場的要求。 但是,現在市場上能賺錢的書、幾十萬、幾百萬本能馬上賣出去的書,難道不是淺薄浮躁的低俗讀物嗎? 無害已經是有益的,更何況還有很多有害的垃圾。 一位北京師范大學的同學曾問我,有那些暢銷書可以看嗎? 我勸她不要看暢銷書。 據我所知,在制作暢銷書的人當中,也有完全不讀自己制作的書的人。 因為他知道不值得。

當然,這里所說的價值,首先是文化價值。 暢銷書和流行讀物不太能承載這種文化價值。 暢銷書和流行讀物承擔的,比什么都有價值,滿足的是網民消磨時間和實用性的訴求。 當然這也非常重要,是我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 但是,出版業以市場為理由放棄文化負擔,眼睛只盯著周期、發行量,這不是國家、民族的悲哀嗎? 我在這里想說的是,市場化并不一定保證出版社只出好書不出垃圾。 相反,由于其尊敬的市場邏輯,也很可能抑制好書的出版,鼓勵和刺激出版無價值的垃圾書。 我們的市場化必須要付出這樣的代價嗎? 還是即使付出這樣的代價,我們也一定要進行所謂的市場化? 電影生產前車之鑒不遠,出版業是否應該特別警惕呢? 在這里,我認為市場化后,出版應該如何實現其文化負擔和社會負擔的問題需要提出。

出版業的文化負擔必須由國家和政府來填補
出版銷售圖書當然是商品生產活動,有市場價值規律。 但是,這個商品和其他商品絕對不同。 其特殊性在于它不僅滿足人們的閱讀費用,還承擔著文化傳承和文化積累的責任。 這種責任在市場行為中不太容易實現,有時相互矛盾。 出版業的完全市場化,作為市場主體的出版經營機構在遇到這種矛盾時會陷入某種不自然的狀況。 在這方面,國家和政府有不可避免的責任。 在過去的體制中,也有致力于以學術圖書、文化傳承和文化積累為目的的圖書出版的出版機構,也出版了許多有利于民族文化傳承和迅速發展的好書。 其背后支持著國家和政府的巨大投資。 考慮到社會文化快速發展的不平衡,大眾支出文化和精英文化必然存在差異,這種支持又是必要的。 我們不希望市場平等地接受流行的暢銷書和學術價值、文化價值高的書。 后者只是國家、政府或社會提供必要的保護。 在西方,來自這種社會的學術圖書和文化價值較高的圖書的保護,往往是通過各種基金來實現的。 在基金會體系不健全、發展迅速的中國,這種保護只能由國家和政府來進行。

但是出版業目前正在進行的這種改革似乎沒有考慮到這些事情。 從受保護出版社的名額分配可以看出,這不是文化思維的產物,而是政治思維的產物。 政治當然非常重要,特別是對以往非常敏感的出版業來說更是如此。 但是文化不重要嗎? 從某種意義上說,文化是政治的基礎,文化是政治的長久保證,沒有文化的政治,只能是矗立在沙灘上的政治。 從這個意義上說,出版業的市場化如果忽視文化的保護,可能會給國家和民族帶來不可挽回的損失。

國家和政府的文化保護必須更加公開和透明
但是,在目前的情況下,出版業的改革已經沒有退路,有人稱之為背水一戰也是正確的。 那么,國家和政府對文化的保護,出版業必須以更加公開、透明的方式完成。 事實上,雖然政府部門在圖書生產和流通上投入的程度很深,相關的優勢鏈也很廣,但是否完全是出于文化保護的目的并不容易說。 出版的書中有相當一部分不僅是政府各部門的文件編纂,也是各級領導的情書。 這其實是對國家和政府資源的巨大浪費。 雖然也有以國家和政府名義設立的各種基金,但在實際運營過程中,往往會失去最初設立時的本意,成為某個行業和部門中人際關系良好的鏈條。 許多有價值的學術圖書得不到足夠的基金資助,分到少量基金的圖書往往缺乏學術價值。 其中的腐敗空之間和可能性可能無法與一些建設工程項目相比,但對腐敗的監控難度可能更大。 由此也可以看出,國家和政府以保護文化為目的投入出版過程的社會經濟學問題相當復雜,絕非外行的我所能指出的。 但是,消除這一弊端的第一步,似乎包含在出版社轉制的動向之中。 出版社分離、脫離政府機關各行政部門似乎預示著國家和政府能夠以更加公開、公正、透明的方式實現文化保護的希望。 這也是作為社會文化管理者的責任。 這樣,出版社的轉制又值得期待。 無論如何,我認為出版業的任何改革都不能以鼓勵好書為目的,損害文化傳承和文化積累這個大目標。
本文:《“解璽璋”》
心靈雞湯:
免責聲明:學習興國網免費收錄各個行業的優秀中文網站,提供網站分類目錄檢索與關鍵字搜索等服務,本篇文章是在網絡上轉載的,星空網站目錄平臺不為其真實性負責,只為傳播網絡信息為目的,非商業用途,如有異議請及時聯系btr2031@163.com,本站將予以刪除。